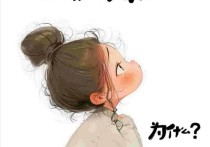寒门再难出贵子?
老李蹲在工地门口扒拉着盒饭,油渍溅到洗得发白的工装裤上。他抬头望了望三十七层的写字楼,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。二十年前他高考落榜时,村长拍着他肩膀说"是金子总会发光",可现在他儿子在城中村小学考了年级第三,班主任却说"要考虑现实情况"。
学区房中介小陈正在给客户算账。他食指在计算器上敲出清脆的响声:"这片老破小每平十二万,但隔壁实验二小的升学率比普通小学高六倍。"穿着真丝旗袍的女士轻轻咂舌,脖颈间的翡翠吊坠跟着晃了晃。楼下卖煎饼的王婶听着头顶飘下来的对话,把给儿子攒的大学学费又数了一遍。
某重点中学的荣誉墙上,优秀毕业生照片在射灯下闪闪发亮。校长室里的鎏金奖杯擦得锃亮,玻璃柜中陈列着校友捐赠的科研专利证书。而三公里外的打工子弟学校,孩子们正在用掉漆的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,载玻片是老师用废玻璃自己磨的。
教育部门的年报显示,农村学生重点大学录取率连续七年下滑。与此同时,课外辅导机构"精英计划"的报名费涨到了每小时八百元。在周末的钢琴班里,穿小礼服的女孩们指尖流出的《献给爱丽丝》,与工地活动板房传来的二手电子琴声,在夏日的热浪中交织成奇怪的二重奏。
夜深了,老李在工棚里用皲裂的手指划着手机屏幕,班级群正在统计暑假研学旅行报名人数。他盯着人均六千元的费用表看了很久,最终在"不参加"后面打了个勾。窗外,写字楼的霓虹灯准时亮起,在夜空里拼出某个国际教育集团的广告词:"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"。